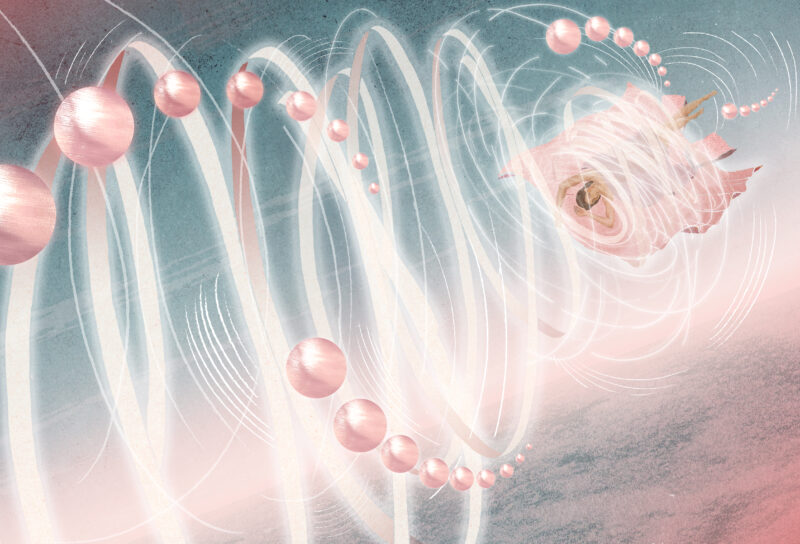迪波列納·柔伊(Deboleena Roy)在實驗室工作時發生了件怪事。她是多倫多大學醫學科學研究所的博士後研究員,她站在無菌通風櫃前,她戴著乳膠手套的手指放在細胞培養箱的門把上。
培養箱內有著數以百計生長良好的大鼠細胞,培養在攝氏37度下。在實驗室的體外實驗過程中,拋棄冗余的培養細胞——畢竟細胞繁殖得很快——並維持一部分的細胞存活以供未來的實驗使用,是一項例行的工作,這工作名為「繼代」(subculture)。
培養箱內有著數以百計生長良好的大鼠細胞,培養在攝氏37度下。在實驗室的體外實驗過程中,拋棄冗余的培養細胞——畢竟細胞繁殖得很快——並維持一部分的細胞存活以供未來的實驗使用,是一項例行的工作,這工作名為「繼代」(subculture)。
在實驗室中,一個生物學家基本上都與實驗對象有著數層隔閡——那對象可能是小鼠、可能是細菌,或是一顆不起眼的細胞。但在那刻暫停之後,柔伊卻抓不到距離感了。
這有一部分和她的工作節奏有關。她每六個小時,就要測量一次神經元細胞週期性荷爾蒙的分泌量;每三到四天,她就得抑制這些細胞的增殖。她已開始感到這種節奏深入她骨子裡。柔伊和細胞們彷彿正在共舞,而這種旋轉的糾葛,一方面讓她質疑自己身為一位科學觀察者的客觀性,另一方面又常驅使她在詭異的時間進入實驗室。「那是凌晨兩點,」當我用 Zoom 與她通話時,她回憶道,「我就在這,扶著培養箱的門——然後我自問:我到底在做什麼?」
如今,柔伊是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埃默里大學藝術與科學學院的院長。雖然她用來換取理論的實驗室工作已在多年前結束——現在她擁有神經科學的雙重職位,並教授女性、性別與性的研究課程——她仍懷念著作為生物科學家的職業生涯。這段經驗,乃是她思想成形的時刻,且在她 2018 著述的《分子女性主義》(Molecular Feminisms)一書中佔有顯著的份量。該書中,她概略介紹了女性主義哲學下的科學、倫理學與廣闊的非人類世界。
柔伊和我說,她的那次暫停不只是關乎罪惡感。作為一位年輕的科學家,她堅持不想殺害動物,但她讓自己接受細胞繼代的操作過程,畢竟這在她的論文研究中是必要的。她在細胞培養箱意識到的危機,源於一陣無預警且令人迷惘的理解:她與這些細胞的關係,並非只有一個面向。這些細胞的生長、分裂與死亡的週期,調控著她的生活。她受著他們的奴役。她對這些細胞採取行動,而細胞也這樣對她——這深深地改變了她的日常生活,且她也越來越不確定到底是誰在對誰做些什麼。
「我是一名科學家,我應該是完全知道我在做什麼的,」柔伊對我說,「但事實上,我認為細胞正在測試我。」
實驗室的情況
在實驗室中,科學家們與細胞一同構建出一種互惠的安排:前者提供或維持那些允許生命存活的條件,相對的,細胞則在新的情況中展露它們的行為。這是一種關係,雖然不算是特別健康的關係。
在社會科學中,有一種新興的共識:任何一種既有的解釋,若是忽略了我們與其他生命形式的糾葛,那這解釋便不夠完整。人類學家已經在他們的田野調查中,涵括了所有非人類的角色——在廣範圍的多物種民族誌當中,追查人類與植物、動物、真菌、細菌甚至是病毒間的生態和文化關係。與此相似的觀點,是否能夠套用到實驗室中受高度管控的生態系統?
柔伊並不算是首位對其實驗對象產生移情之苦悶的生物學家,而這種因糾葛而生的複雜情緒也不是新鮮事。細胞遺傳學家芭芭拉·麥克林托克便相信:培育出她所謂的「對生命體的感受」是成為一位優秀科學家的重要因子。麥克林托克的指標性工作,就是在二十世紀中葉證實了遺傳學上染色體的準則;她發現了遺傳物質的流動性,此領域起初冷僻不受重視,但最終於 1983 年獲得了一座諾貝爾奬的肯定。
她選擇的生命體是玉米,這生物五彩繽紛的顆粒生動地表現出植物的遺傳性狀。那麼多年過去,她越來越熟悉——並抱著「無比的愉悅」——冷泉港實驗室的實驗玉米田中每一株植物個體,她在該處進行了超過五十年的研究。她的植物的生長與死亡的週期,比其他用於研究遺傳學的實驗對象——例如果蠅——來得長。這讓她有充分的時間理解這些繁茂的植物,並得以近距離研究它們。
在顯微鏡下,她也同樣地沈浸在玉米染色體的隱密世界中。一如她田裡的植物般,它們總是在變化,且對於環境的干擾相當敏感。她學會了區辨不同類型的變化及它們之間的細微差異。她不贊同其他科學家企圖在他們所見的事物上「強加一個答案」,她寧願化身成「系統的一部分」,且讓答案自然來到她面前。伴隨著長時間的觀察與耐心傾聽,並抱持著允許植物為其自身發言的開放性,麥克林托克培養出極其卓越的敏感度,去察知她那些非人類合作者內部的細微變化。
這種敏感度很罕見;這為麥克林托克贏得了神秘主義者的聲譽。當然,麥克林托克僅有的魔力,就是耐心地在最平凡無奇的發現中觀察出生命的奧秘。
有不少人士通過人工手段,提高感知以達到相似的狀態。反文化(countercultural)的指標人物伊莉莎白·吉普斯,在一篇描述她初次嘗試LSD經驗的文章中,提及自己在樹下坐了數個小時動也不動,檢視著一種無比微小的蟲子。「這小到不行的綠色蟲子攀附在草葉上,其體型之小簡直讓蚜蟲顯得像巨人,」她寫道,「我過往從來沒有看到過那麼小的東西。」
這種觀察,雖然離實驗室甚遠,卻與麥克林托克作為科學家所理解的道理相吻合:你越靠近,且越願意去觀看這個世界,它就能讓你看到更多。
一如撰述麥克林托克傳記的依夫林·福克斯·凱勒所記載的,麥克林托克長年下來與玉米的緊密聯繫中所發展出的深切親暱,在字面上或象徵性上都拓展了她的視野,允許她觀看人類極限之上的東西,深入玉米代代傳承中所發生的細微基因變化。這並非是捨棄科學的客觀性——這是一項盡己所能的科學家堅持觀察的成果。而另一項並非有意的成果,便是對萬物彼此之關聯性的卓越感知力。一旦她培養出了對玉米的密切聯繫,也就變得難以去掙脫她自身的束縛。「基本上,萬物皆為一體,」麥克林托克和凱勒說。「每次我走在草上,都感到很抱歉,因為我知道草正對我尖叫。」
在分子女性主義中,柔伊拓展了麥克林托克的一系列提問,探索科學分類學的理念本身,並試著去繪出生物體之間的界線。她質疑,分類學不僅將人類從自然界被剝離開來,並在沒有階級的地方創造了階級。沒有所謂的存有之鏈(great chain of being);所有具生命之物皆彼此依存。「問題可能不在於人與動物、植物、水和無機元素等之間有無差異,而在於我們怎麼去思考這些差異,」她寫道,「我們要選擇將這些差異視為等級的差異,還是種別的差異?」

重新考量階級
我們選擇為各類差異分配價值。不過比起想像我們自己位於生命階級的頂峰,還不如簡單地將我們自己置於基礎層,延續一片連綿的平面。轉移優勢的視角,或許能協助我們更清晰地辨識出我們與萬物的糾葛。我們與玉米不同,但許多人類的文明種植都依賴玉米存活。我們與細胞不同,但我們由細胞構成——更不用說那些住在我們腸道、喉嚨和皮膚的微生物集團了。正如女性主義作家與哲學家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所觀察到的:「成為一,乃是與多者共同成為的。」柔伊在此呼籲與非人世界組成一連續體(continuity),也許是一種哲學上的挑釁,但仍是一強有力的提醒:我們是生命在自身上的行動。
柔伊建議,與其以分類學觀點去問生命體是什麼,不如問它能做到什麼還來得更有益。在歷史上,科學一直依賴著固定的身份與本質,但生物學家的工作,讓柔伊接觸到了「物質行為者」——各類活著的東西如基因、荷爾蒙、細菌與細胞——並更加有用地將此描述為過程(process)。你越深入顯微鏡觀察,那條畫在主體與觀察者之間的線就變得越擺盪,而生命本身也越顯示出是由我們所共享的變化之潛力所定義的。柔伊寫道:生命,是一樁事件。
然而,生物學並非如此。正如福克斯·凱勒所指出的,現在西方科學的世界觀,根植於笛卡兒的機械論視野——他將一隻受傷的狗的吠叫比為一架不具正常功能的機械發出的聲音——與法蘭西斯·培根的言論,如同福克斯·凱勒在一篇富影響力的論文中寫到的,「將對自然的統治以及自然作為女性的矜持形象結合起來」。這個將科學視為一種控制與馴服無情世界的過程的概念,其影響力已經橫跨了數個世紀。但如同麥克林托克的工作所展現的那樣,科學家也可以選擇與自然展開對話,仔細聆聽它的回答。這種方式,長年以來都是原住民對於現實的觀點之一,他們透過互惠的關係來看待世界。
我們都與這活生生的世界糾纏在一起,而研究此事的人更是如此。有時這種糾纏感覺起來像是親密交流:一個足夠敏感的科學家會開始感覺到草在向她尖叫。芭芭拉·麥克林托克被邊緣化數十年,直到分子生物學家證實了她刻苦的觀察。
卸除科學主導的衝動被許多學者詮釋為一種女性主義的計畫,但這也相當於是學習去面對一種感受——去感知不穩定、變化與互相化成(mutual becoming)。在以結果為導向的研究世界中,或是承擔著來自機構要求發表具體發現的壓力下,還得去接納這種不確定性,這是很詭異的事。柔伊擁有探勘這些疑問的自由,部分原因在於她是一位跨領域的學院人士。但花一番工夫去感受生命體的整體,並非只是一種哲學上的立論,還能有實質的優點。
莎拉·理查森是一名分子生物學家,她的生物工程新創公司「MicroByre」馴化了野生細菌以提供工業用途。正如麥克林托克,她也傾向於讓生物為其自身發言,並研究這些細菌從哪來,是什麼促進他們的行為,他們需要什麼以便成長。比起掌控細菌,毋寧說她馴養他們——期許人類與細菌在改良後的共生關係中能協同工作以製造有用的物質、分解廢棄物並拯救這個世界。
當我們在 Zoom 上聊天時,她的貓在螢幕上前前後後展示尾巴像個衛兵。她指著她的貓並解釋道,馴養是讓彼此受惠的安排。生物學家不需要去濫用大腸桿菌和酵母菌等模式生物,迫使他們超出其自然具備的能力,畢竟世界上有那麼多野生的細菌能夠完美地勝任這項工作。她說,他們只需要一點移情(empathy)來加以安撫。遇見野生細菌,就像初次接觸外來種時得進行協商一樣。「你必須每次都去了解他們的脈絡,而且你必須要拋下一點自我才能做到。」
理查森希望能訓練野生細菌,直到有一天他們能將未使用的生物質轉變成石油產物。麥克林托克發現了轉位子(transposon),這是一種可以在基因體中變換位置的 DNA 序列,這發現遠早於發明基因定序技術之前。柔伊的細胞繼代過程,協助她發現雌激素受器、雌激素分子與腦中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GnRH)神經元三者間的新型交流形式。這些科學家都展示出各種接觸非人類世界的方法,而且甚至還能讓他們為我們勞動,但這些都來自於對生命最根本的尊重。這僅只需要在權力上重新協商,並有意願去將實驗室中的同仁——不管是細胞還是整個生命體——視為合作夥伴。
移情不只是關乎生與死的問題,還是一種導引我們去對實驗室內非人類的工作同仁提出新問題的方針。理查森告訴我們,她努力變得更體貼,但她也不希望感到窒礙難行。與此相對,她想透過移情來驅動她對其所研究的生物的好奇心。「移情需要少一點,不是想著『喔混帳,我要殺光他們』,」她說,「而是進一步去想,『為什麼他們當初要做那件事?』」
接著我開始聊到對芭芭拉·麥克林托克的觀察,但在我說完之前,理查森就中斷我的話,她點點頭且說:「對生命體的感受。」她告訴我,當她還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分子生物實驗室內的一名高中生時,她很幸運地接觸到了麥克林托克的觀點。雖然她的新創公司將自動化與機器學習整合到產業製程中,但理查森察覺她自己正在實驗室內對每一個生命體培養出一種感受——正如麥克林托克所為。
她表示,如果你想在生物工程上取得成功,那麼,與生命協作將會比抵抗來得容易。在生物學中,敵意往往會演變成交流,而且許多基礎的生物學過程,都是從互相抵抗漸進成共生當中孕育出來的。生物體之間的合作關係或競爭關係,都可能會驅動演化。雖然我們並不總是能徹底理解共生的本質,但我們也讓他們為我們勞動了數個世紀——從馴養狗和貓,到玫瑰的育種,到將野生包穀轉變為玉米。
理查森將她的筆電攝影機鏡頭轉向一側,整個螢幕都是她那隻睡著的貓。「當狗搖尾巴的時候,代表一件事;當貓搖尾巴的時候,則代表另一件事,你必須察覺這件事。」她說,「一開始弄清楚這件事的人是生物工程師。我們需要去記起那些在我們的意識中,以生物學家和生物工程師的身份提出這些想法的人。他們教導了我們對生命體的感受。」她深情地注視著她的貓且說,「這就是為何我會獲得這隻小傻瓜。」
當我們馴養其他生命形式時,我們便是在商議出一項合約:以食宿來換取衷情、寄託與守護。但我們與我們的寵物都並未被這項合約定義。正如任何貓的飼主所表明的:即使是最溫馴的虎斑貓,也蘊含著神秘。
柔伊表示馴化的過程會導致盲點。「在我們所有的實驗室裡,我們已經馴化了大腸桿菌,並想著我們將去利用這生命體的機械部分來達成我們的目的,」她說,「至於在這生命體上,我們尚未注意到的其他生命面向呢?」
在柔伊的書中,她指出生物學家、遺傳學家和生物工程師已經按照一項前提建立起他們的專業,此前提是:生命是一種可由生命體如細菌來進行編輯、重寫與翻譯的一種文本。在合成生物學的實驗室中,大腸桿菌乃精確地為此目的——轉錄DNA 並轉譯RNA——所育種出來。然而柔伊表示,「一旦細菌完成了他們在轉錄、重組或基因編輯的任務之後,他們很快地就會被殺滅以便取得他們體內富有價值的蛋白質。」
她表明,藉由一種機械論的視角去接近這些研究室同仁,將使我們錯失良機——畢竟我們認為他們只有在具備生產性時才值得關注。而我們對待微觀世界的方式,會反映出我們對待宏觀世界的態度。「我們認為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優秀,」柔伊說,並示意出分子生物學的歷史及其在優生學上的角色。「我們曾認為人類的某些特徵並不具價值,或是不具備生產性,這是因為我們無法去理解或欣賞這些特徵的用途。」
當我們質疑等級或分類學時,即使是在分子的層次上,我們便是在從事一種激進的謙遜行動——此事也彰顯在我們的人際關係中。柔伊說,這是整個生涯的事業,去將自己視為多者中的一員。馴順、野生、主體、觀察者:我們都以自己的方式,成為生活模式的載體。藉由蓄意將人類去中心化,我們只會變得更富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