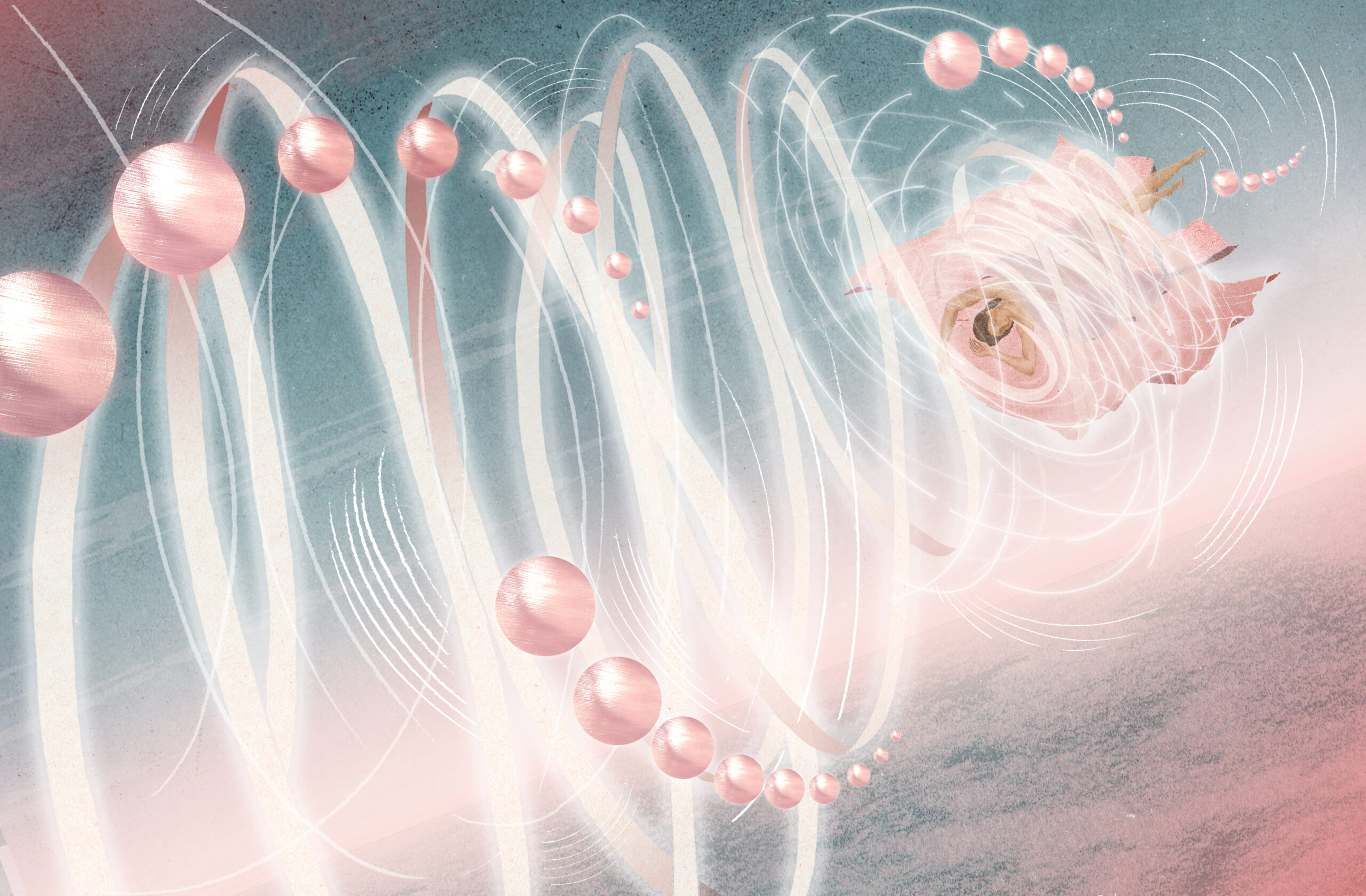家蠶蛾並不華麗。如果你在博物館的展示中,途經其中一種被釘在同科其他成員旁的,經馴化的蠶蛾標本,你可能不會想到要停下來看。家蠶擁有米白色(不怎麼像奶油色,也不像煙灰色)的肥大身軀,淡淡的棕色斑紋與羽毛狀觸角。歷經五千年的籠內飼育後,此種成蟲已不能飛或進食。不過他們也很少有機會做這些嘗試,畢竟他們泰半在幼蟲階段就被殺死,死時被包在柔軟的繭內。像龍蝦一樣,這些蠶乃是被活活煮死,而熱融斷了繭與幼蟲間的聯繫。很快地,繭只會剩下一枚空殼,並供人繅出長而白的纖維,即廣為人知的「絲」。這種令人不快的過程如何產生那麼美的東西呢?
我習慣把昆蟲想成是害蟲,疾病的媒介與番茄的競爭對手,但若能把牠們想成是我們的小夥伴更好。他們吃我們,我們吃他們,我們一齊演化。而那些犧牲自己以便製造絲線的昆蟲,則對我們特別好。全球各地的人類從公元一世紀開始,就已經會使用蜘蛛絲來包紮傷口,即使此法如今不再常見,我們也仍會利用蜘蛛絲來縫合皮膚層和內臟碎塊。絲中的結構式分子相容於我們的身體;我們的細胞不會立刻將其辨識為外來的入侵者並策動戰爭。我們能藉此纖維癒合傷口。
這些蒼白的絲線協助我們脫離古代。絲的發明,簡化了現代世界的經濟發展,因為透過絲的貿易,金錢、知識和權力的持續流動,已橫跨在地球最廣闊的大陸上超過千年。絲路形塑了今日的地圖、邊界,甚至宗教。作為核心的織品,改變了人們的穿著、繪畫與書寫方式,並啟發了各種傳說、詩句與歌謠。其中原因不難看出:絲具有稜柱型的光澤,此乃是基於蛋白質的三角架構堆疊而帶來的視覺把戲。
我有一件絲質的襯衫,在燈下閃耀著光輝;它薄如蟬翼,太過精美而不便穿上。而想到這絲線的製造之處,位在吃桑葉的幼蟲的唾腺中,便覺得有點荒唐:它一開始是液態的漿狀蛋白質,而在空氣中硬化。當我寫到這,我便想像著我躺在床上數個小時,不斷啐出粘膩的液體,且在我身體周圍硬化成又大又長的泡棉管,將我一圈一圈地整個包裹起來,使我能安全地準備好溶解身體並生成翅膀。此事很詭異,彷彿格雷戈爾·薩姆沙的肉體變異。但這也是美來到此世的方式,透過分子結合與鍵結的斷裂、膠合與去膠合。
一旦美顯現其自身,人們就會情不自禁地將它化為神話。這些創世神話掩飾了為美做出的犧牲,並且略去了所有的膠狀物與黏稠物。在這類型的神話中我特別喜愛其中一則,儘管我發現這不太現實。在故事中,我們會看到一位受帝王寵愛的妃子穿著她日常的華貴衣著,坐在由扁薄的桑葉構成的樹蔭之下。她聽見了細微的輕響,並在她的茶杯中看見一隻蟲。嚴格來說,那並不算是一隻蟲,而是鬆散的某種小東西浮盪在她的飲料內。當她將那東西從中撈出時,注意到那絲線既奇異又強韌。這使她意識到一件事,她抬頭看,見有更多的蠶蛹包裹在柔軟而富於光澤的繭內。她知道接下來該怎麼做,她喚來僕從,且說:紡吧。
我們並不清楚究竟是在何時開始生產絲,但經推測,有可能在八千五百年前便已出現。歷史學者評估它是在公元前 200 年前後,從中華帝國傳播出來。我們搜集到的一些物件講述了這些故事,提及早期的蠶蛾育種者和蠶絲業製造者,例如在中亞出土,由大英博物館永久收藏的一件一千三百年前的備忘用文物。這塊木板上繪製著四個人物,其中一位是配戴有精緻頭飾的公主,端詳著她珍藏的桑蠶、桑樹種子與工具。鄰近的一位侍女戲劇性地指著蠶絲公主,要人們注意她的伎倆。而在公主的另一側,一個男人正坐著並編著絲織品。
這件腐壞的人造物,很可能是由一位故事講述者用來向大眾解釋這項奇蹟似的發明,如何從一個國度傳播至另一個。你瞧,此事的發生並不在預料內。中國想要維持其壟斷狀態,因為這紡織品的利潤高得不可思議。但就像其他的重大發現一樣,這東西就是好到根本藏不住。這畫中的一景,不僅被歷史學家尼爾·麥克格雷稱之為「史上最偉大的技術盜竊之一」,也被納入蠶絲之神的管轄之下:他顯現並贊同這位公主大膽的時尚選擇及其扭轉經濟的效應。
這兩則故事都揭露了一些蠶絲的重要之處:這種織品與財富和權力有著如此繁複的糾葛——即使這是由社會底層的人們養育、收穫並紡成的東西——但我們不大能推想出這些事物如何在蠶絲的發現與傳播上造成衝擊。但他們確實造成了影響。從一開始,這些底層的婦女就在收穫並紡出這些絲線。在古代的中國,這些婦女並不被允許穿上她們生產的絲綢,這些織品都是製造來提供給社會上層人士的。這情形在往後的三千年間有了一些變化,但變化的程度倒也沒有你想得那麼多。蠶絲仍主要由貧窮且無法負擔絲織品的婦女們生產。蠶絲的歷史,與其說是一則持續演變的技術的故事,不如說是一樁案例研究,述及特定的主意如何能夠跨越國界與海洋而傳播開來。在日本,蠶絲的製造大約是在公元前三百年開始,且就在兩百年後傳入了羅馬帝國。在公元一千年,北非與義大利出現了桑蠶業。在中世紀,義大利的蠶絲主導了歐洲的市場相當長的時間,但不久後,法國迎頭趕上並開始自行製造美麗的織品。十七世紀前葉,英國人也在種植桑樹,希望能夠養出他們自己的桑蠶。緊接著,1613 年,載著桑蠶幼蟲與桑樹種子的船隻抵達了維吉尼亞州,準備好將另一種潛在的害蟲引入「新世界」。每個國家都在紡出自己的織物,探索新的編織、染色與穿著的方式。
絲路在解體之前,仍持續在貿易中扮演著特定角色,畢竟中國仍是世界上最頂尖的桑蠶與生絲生產國。此外,中國還有其他令人驚豔的發明可以分享給全球——紙、火藥和瓷器。而且歐洲人又從不停止對異國香料的渴求。有些歷史學者質疑:香料才是主要形塑所有重要貿易路徑之物,而非蠶絲,但要重新命名這整樁事件,恐怕有點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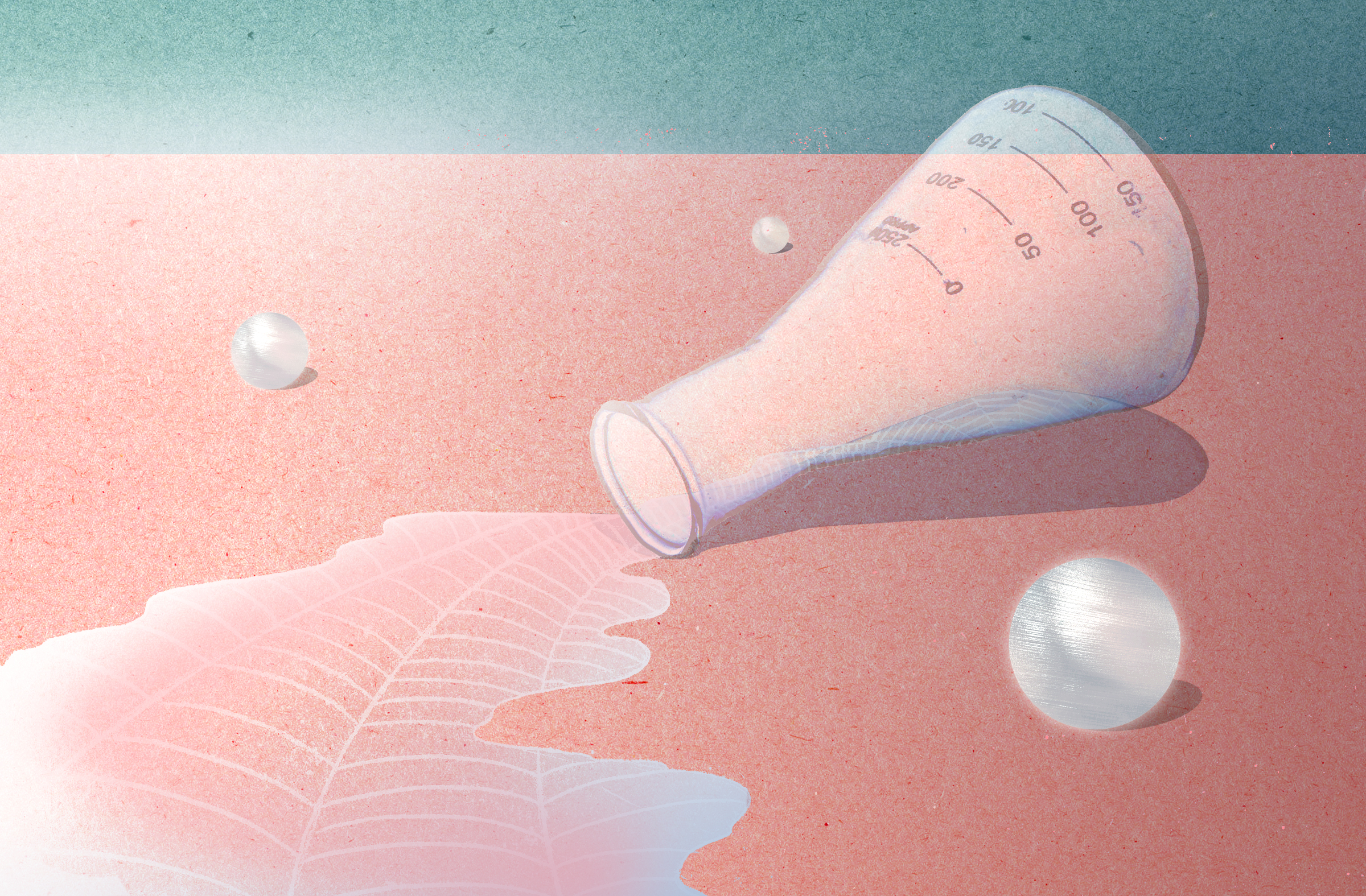
幾個世紀以來,人們一直在嘗試去創造可以代替或媲美絲綢的織品。在某些地區,對絲替代品的渴求比其他地方更加迫切。像在英國,由於種植了十萬棵錯誤類型的桑樹,使得他們的桑蠶業難以啟動。而在十九世紀的法國,兩種疾病的發生幾乎剿滅了整個國家的桑蠶,且由路易·巴斯德驚險地扭轉了這個災難。
有個科學家不再去煩擾那些桑樹,而是開始去把玩木漿。在 1880 年代,伊萊爾·德·夏多內(巴斯德的助手)用纖維素創造出了一種人造絲。這東西在 1900 年代初上市,名為「夏多內絲」或「婆婆絲」。夏多內的發現,帶來了許多不同形式的基於植物原料的合成織品,從天絲到竹纖維等。雖然嫘縈還算可以假裝是絲——至少在一定的距離之外——但卻未能擁有同樣的光澤,且其從人體上懸垂下的樣子也與絲很不同。
由於美,由於其象徵性的意涵,以及其在醫療上的特徵,絲至今仍存。即使如此,基於很多良好的理由,讓一些人試著將昆蟲從製造蠶絲的方程式中移除。首先,我們並不需要煮死那麼多幼蟲,這可能對牠們是項善舉。此外我們也有可能運用其他類型的蟲絲,例如蜘蛛絲或蜂絲。這些絲的織品強韌得不可思議,而且藉由正確的編織與層疊法,甚至可以用來製造防彈衣。我們在養殖蜘蛛上做了很多嘗試,但從未成功,因為蜘蛛是個不受管束、態度不佳的食蟲者。這是我們的損失:蜘蛛絲比蠶絲更強韌,可用來製作各種東西,從登山繩索到人工韌帶、人造骨骼到其他身體部位等。
此外還有另外一個良好的理由,讓人重新思考這古老的方程式。如果用谷歌搜尋「蠶絲工業勞工侵害」,就會在你面前揭露一段讓人心痛的歷史。2003年,一份人權觀察報告記載了在印度長年以來對於奴役女孩的不當對待(含性侵害);在2020年,一份美國駐烏茲別克大使館的報告,指出「強迫勞工養育蠶繭」和「商業性剝削」,並列為「明訂最惡劣的童工形式」。在美國,我們都傾向於認為奴隸制已是過去的事,既遙遠又罕見。但正是現在,還有奴隸,正從事收穫蠶絲的工作。這勞動的最後,是新娘服裝套組中一件光澤閃耀、飾有精緻花朵的白色睡袍,或是一張柔軟的毯子,鋪在托兒所的地板上,給名叫弗列斯特(Forrest,意為林中居住者)、皮斯(Peace,意為和平)或甚至叫摩貝莉(Mulberry,意為桑)的孩子使用——這種怪事總會發生。
拜合成生物學的工具所賜,在數年之內,我們有可能可以穿上無蛾、無蟲的絲織品。我們不再需要去養育幼蟲、等到他們結繭,我們可以簡單地將基因從桑蠶(或蜘蛛)身上取出,植入另一個生命體內,並且讓這些新的、經改造的生命體來給我們製造蠶絲。我可能稍微失之輕率,因為這在我聽來像是科幻小說,但多個實驗室與公司已花了數十年在處理這些特定的問題。基因可以像拼圖片一樣移動,也可以像卡片一樣交易。或者我們用個更常見的譬喻:生物可以透過編程來執行新的功能。我們已經製造出能在黑暗中發光的老鼠,也藉由從翠雀花與三色堇上偷來的基因來製造紫玫瑰(通常商品名為「藍玫瑰」)。於是,利用酵母菌或細菌來大規模製造蠶絲,倒是不會比那些迷幻的創作來得更詭異。
但此事也有壞處,人們將因此受苦。根據國際桑蠶業協會(International Sericulture Commission, ISC)的意見,此舉將會威脅現今位於中國、印度和泰國雇用超過八百萬員工的工業。這些工人大多都住在農村,其中泰半是婦女。ISC 認為桑蠶業是良好的事業,因為它讓「鄉村人口能就業」,避免了「人口移動至大都市」,且「僅需少量投資」。
這些權衡已超過了我的能力範圍,但我還是會關切人們是否會突然中止養育用來製造蠶絲的桑蠶蛾。當我們像古代人那樣用手製作東西時,我們會學習到一些事。我們參與了這波關於美與創造的潮起潮落。煮繭、獵鹿、伐木——這些行動都帶有粗暴的元素和美的潛質。而這些事也都有替代方案。我們可以購買實驗室生產的蠶絲、實驗室生產的肉,並使用完全工程化材料(entirely engineered materials)來打造我們的家園。這對環境更加友善,且此事甚至也能被視為一種傳統。不管如何,現代的生物學實驗室,只是人類驅動演化的新前沿,並應用了一切已存在的事物。替代方案並不一定代表著取代。若我們曾經學會什麼,那就是:單一文化(monoculture)難以存續。
或許這裡面的答案,也包含對培育的桑蠶蛾抱以敬意,並讓所有從事收穫蠶繭的人得以擁有尊嚴,但這兩者至今都尚未出現。至今我們所擁有的,只有故事與產品。美麗之物,重要之物,而當你試圖抓取這些從掌中滑落之物,它便閃耀光澤,隨即失色。